时间:2021-08-16 14:36来源:天津日报编辑:文化产业导刊

向迅 1984年出生,现居南京。出版散文集《谁还能衣锦还乡》《寄居者笔记》等。曾获林语堂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评委奖、孙犁散文奖、冰心儿童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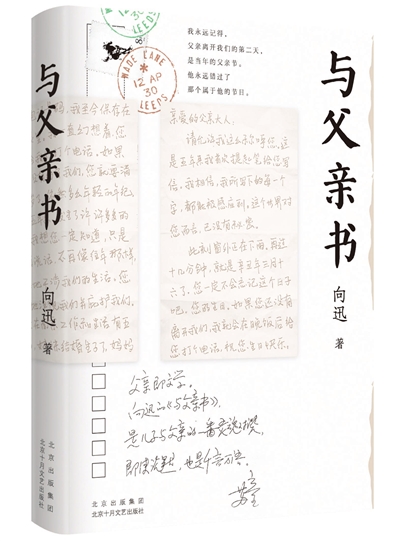
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武汉卓尔书店联合主办,作家向迅、李修文围绕《与父亲书》《诗来见我》,就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散文写作的边界等问题展开深入对话,并通过视频直播。
《与父亲书》由六篇散文构成,向迅选择父亲生命中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书写父亲在童年、饥困时、病重后的生活琐事和生命状态。这是他写给父亲的深情之书,是儿子与父亲的灵魂对谈,呈现出一位中国农民父亲的坎坷命运与精神秘史。
这位父亲远离脸谱化光环,以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淹没、被遗忘的失败者身份,回到文学作品中。他勇敢、热情、善良,却又暴躁、冷酷、胆怯,他早年面对困顿的生活满含悲愤,晚年面对疾病饱尝孤独……作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形象,赋予这个形象普遍意义:每一个人都能在他身上窥见自己父亲或父辈的身影。这是一本献给父亲的书。
著名作家李修文对向迅的《与父亲书》给予高度评价:“向迅那么冷静、客观地呈现生活复杂的片段、细节,最打动我的是书中的父亲晚年身患重病下楼困难,嘴巴里不断发出若有若无类似于号子般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生死之间到底经由什么样的撕扯,最终呈现出什么样的存在。”
向迅坦言:“我渴望写出不一样的父亲,而且有小小的野心,想让读者在他身上窥见自己父亲抑或父辈的影子。这可能是一种奢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位不加美化和修饰的父亲如实地写进文章里。”
向迅曾多次获得国内各项散文奖,评论认为,他在《与父亲书》里袒露出年轻作家通过写作,使散文这种文体不断向前进步的可能性。向迅说:“现代散文历经百余年,随着文体越分越细,它的边界越来越窄,作家能钻研的东西也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的散文写作急需改变。李敬泽、于坚、刘亮程、张锐锋、宁肯、周晓枫、李修文等作家改变了当下散文的写作方向,我也一直在追求变化,想拓宽它的边界,这在《与父亲书》里面有所体现。”
我们想极力隐藏的部分
可能恰恰是最具文学性的
记者:最早您是因为父亲生病去世,才想到要为他写一本书吗?
向迅:关于《与父亲书》这本散文集,先后间隔了五年。最早的一篇是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陪护结束回到江苏,把一些细节性的东西记录下来,当作一个长篇非虚构的作品。可能在创作过程中需要面对一些事情,我还是不能完全去面对,所以后来没法写下去。这本散文集里有两篇文章就是那时候写的,可以单独成篇。
我们的父亲作为个体的人,都是无名之辈,数千年以来都是如此。我父亲作为农民,可能他的生命失去了,就失去了,包括他的亲人,除了每年特殊的日子会想起他,其他时刻他都是被遗忘的。一个村庄也好,一个城市也好,每天都有很多人逝去,我们能够想起谁呢?我们自身也是一样。所以,我当时就想为父亲写点东西,不能让他像我们村子里其他人一样,消失就消失了。我觉得,我写父亲是为了维系历史,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一代接一代人延续下来的,我们每个人的父亲都是其中的一环。我有点紧迫感,因为随着时间流逝,我现在回忆父亲在同济医院、在家里的细节,很多都想不起来了,后悔当时没把它如实记录下来。
记者:有些作者在写逝去亲人的时候会带着眼泪,感情越深心情越沉重,您也是这样的吗?
向迅: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确也没有朝这个方向想,更不想赚取读者的眼泪,我就是想客观、真实地呈现我父亲生命中的那些时光。我可能渴望写一个不一样的父亲,虽然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遭遇都比较雷同,但作为生命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肯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方。我渴望把我父亲最真实的一面体现出来。王安忆有一篇写她父亲的文章,名字叫《父亲从哪里来》,其中写到一段,她说我们最熟悉的人可能被忽略掉,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是柴米油盐,我们可能把父亲的情绪给忽略掉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自以为对他了如指掌,但真到了写作的时候,才发现对他真的是一无所知。我们真正了解他们吗?真正了解父亲、了解母亲吗?当我写父亲的时候,的确需要勇气。
这本书的几乎每一篇,我都用了十二分力气。最熟悉的人最难写,这条不成文的写作定律,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深刻体现。要把父亲的形象从日常事务中浮现出来,首先要把他还原到日常事务中去。而要还原丰沛的日常生活细节,则要带着放大镜沉入到往事中。
记者:您在写父亲的时候,会做怎样的取舍?您希望呈现给读者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向迅:有一些亲情散文为什么受到诟病?因为我们写的时候,对我们的亲人可能会“手下留情”,可能对他进行美化、修饰,把他不怎么光亮的部分隐藏起来。而在我的散文中,会尽可能地把最真实的生活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想极力隐藏的部分,可能恰恰是最具文学性的。包括我把父亲面对疾病的胆怯、恐惧,都呈现出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我的父亲。我们从小学写作文开始,父亲可能就是很完美的人,充满力量,像英雄一样。随着成长,我们发现父亲可能并不完美,可能有落魄的时候,可能遭遇生活中的打击,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父亲?作为文学从业者,应该把他真实的部分呈现出来,这样才能体现父亲的多面性。我想打破传统散文中对父亲的歌颂式写作,我觉得那种写作不够真实。
在写作中与父亲和解
父亲的形象愈发清晰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和父亲的关系并非完美。
向迅:作家写作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和解,包括与自己和解,我写《与父亲书》的一个原因就是与父亲和解。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与父亲有很多冲突,有很多不理解。我父亲特别严厉,脾气暴躁,我们小时候经常挨骂,我们胆小如鼠。我们和妈妈几个人在房间里聊天,谈笑风生,父亲一进来,我们立即就正襟危坐,笑容也收起来,很怕父亲。卡夫卡在1915年给他父亲的信里提到的对父亲的那种恐惧,我觉得跟我一模一样。我后来离家上学,就是想摆脱父亲。但是在童年时期,我对父亲还是崇拜的,他个子很高,在我心里像是无所不能的英雄,只不过后来我到了叛逆期,觉得他什么也不懂,就想离开他,越远越好,所谓逃离父亲。毕业后我一直在外面生活,随着经历的增加,对父亲有了重新认识。但是我和父亲的沟通存在很大障碍,基本没有交心的时刻,包括他生命快要结束时,我想与他交流往事,把他在外面谋生,经历的一些最极端的事情讲给我听,但我没有勇气对父亲说:我想与你谈一谈。
记者:您写这本书也是和父亲的一次交流。
向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这个目的也达到了。因为很多农民都像我父亲一样,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一辈子就是养家糊口,再建一栋房子。但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我父亲还是有理想的,即使在他生病之后,他还对我讲,等病好了,回去把花园建好。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我父亲很爱花,他无论去哪都会收集花种,回来种在我家花园里。他带回来的格桑花种子,不仅在我家花园开了花,在所有我们家族的院子里也都开了花,每到春夏时,一片姹紫嫣红。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交不起学费,我就怪父亲:“学费也不贵,怎么交不起,你们怎么没有志气?”后来我反思,我父亲真是挺伟大的人,他没读过什么书,却把我们兄妹几人都相继送去读了大学。我后来了解到,我父亲特别聪明、有才华,如果他能多读书,可能会成为艺术家,因为他真的无所不能。我外婆就是觉得我父亲手艺好,养家没问题,才把女儿嫁给他的。
那时候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和母亲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跟父亲最多说五分钟、十分钟,就没什么话说了,有时还会沉默。有一次,父亲甚至在电话里问,怎么跟我没有话说?我虽然真的跟他没什么话说,但他在我心里还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去世后,我可能表面上并没有多么难过,但我总会梦见父亲,梦见他还活着,他的离开的确给我心里留下了一道无法弥补的伤口。卡夫卡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写作就是想写我无法扑在你的怀抱里,无法哭诉的话。”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可能有一个潜在的动力,就是说给他父亲听。我写《与父亲书》可能也只是一个开头,后面还有许许多多关于他的事情,可能还会写。
最高级的写作
就是个人化的叙述
记者:有一句话说,如果要了解父亲,可能自己成为父亲之后,就自然而然地了解了。
向迅:我们的父辈,可能都不善于在儿女面前表露真实想法。如果你想改善与父亲的关系,很多时候你站在父亲的角度思考问题,可能就会明白。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给他写一封长信,把你内心的犹疑不解告诉他,他可能会对你内心的想法有一些理解。
记者:您写小说、诗歌、散文,特别是非虚构和小说之间,如何划分边界?
向迅:我以前写纯文学的散文,最近几年一直在追求变化,在《与父亲书》里面有所体现,有的篇目可以当作小说读。司马迁的《史记》,不能说它是散文或者小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超级文本。还有先秦诸子百家的作品也是,不能用散文或者小说来界定文体。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散文面临革命,需要打破边框,所谓小说、散文、诗歌,可能变成存在于我们思想里的一个东西,我们想怎么改造就怎么改造,我不想把文体分得太细。我记得《小说月报》曾有一个栏目,就是容纳一些无法归类的实验性的文体。
记者:像您这种个性化的写作,您认为如何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您怎么评价通俗文学?
向迅:我觉得最高级的写作就是个人化的叙述,因为他想要摆脱大众化的叙述。卡夫卡在生前没有什么读者,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尤利西斯》也是,但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读,因为它的文本很独特。个人化叙述也可以和个人腔调结合起来,作家追求自我的声音,如果没有自我,容易被大部分声音淹没。我常说叙述腔调,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有迷人的腔调,别人模仿不了,所以他成为了马尔克斯。通俗文学可能会风靡一时,读者甚多。不过在我看来,现在文学界认同的还是写得比较严肃的、有个人声音的文学作品。
向迅
我与父亲
父亲曾给我写过许多封信。那些信,寄自北京密云,贵州某县,乌鲁木齐,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我据此知道父亲正在哪里谋生。每每有他的信被邮差送来,我都会怀着隐秘的喜悦,躲到一个无人打扰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抽出两三页叠在一起的信纸──多半是从笔记簿或练习册上裁下的内页──展平折痕,逐字逐句读。
父亲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陌生的一面。这个父亲,就像是换了一副嗓子,换了一个性格,换了一副面孔,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了许多平日里听不到的话,甚至还有点啰唆──在他嘘寒问暖的时候。而且每封信的开头,他总是模仿古人的笔调:吾儿向迅,近来可好?读着这样的句子,总觉得怪怪的,令我忍俊不禁。
我所熟悉的那位父亲,是一个出了名的直性子和暴脾气,不会花言巧语,更不会虚与委蛇,与人理论,八成会擦枪走火。在母亲面前,他极少表现出作为丈夫的温柔;在我们兄妹面前,他也极少表现出一位父亲应该具备的耐心。而在信中,父亲真的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他朴实无华的措辞中,我不仅充分感受到了他发自肺腑的关心与爱意,还感受到了他作为父亲的无奈与悲哀,我甚至还隐约感受到了他为试图敞开心扉与我沟通而做出的巨大努力。信中的父亲与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恰如地球的南北两极,也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父亲,立体的父亲。这个父亲,有幸被我看见了,读到了,感受到了。而哥哥和妹妹,只看见父亲的一个侧面;母亲或许也是如此。
我曾把父亲写给我的那一摞信件视为珍稀之物。我把它们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从江汉平原带到珠江三角洲,又从珠江三角洲带到湘江之滨。正是在湘江之滨,我开始书写父亲,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某一日,我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把父亲写给我的那些信件和其他一些比较私密的信件,悉数销毁。我把它们撕成碎片,扔进了垃圾桶。
2015年春天,我计划为父亲写一本书,第一时间就想到那摞信件正是最佳的创作素材,可任我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父亲写给我的只言片语。冷静下来,我才想起前几年做过的蠢事,后悔莫及。
一年之后,那摞信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那年夏天,父亲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果那些信件还被我完好无损地保存着,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阅读每一封信的时候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父亲。否则,我们就只能通过回忆了。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父亲的记忆会越来越模糊。我要通过书写的方式,让父亲活着,让他逐渐模糊的形象重新变得清晰起来。这既是我理解父亲的方式,也是我怀念父亲的方式。
对我而言,尽我所能写出父亲一生的故事,就是在履行“保持时间的回忆”“维系历史”的义务。如果我不及时把那些与他有关的记忆碎片从深海里打捞而出,它们将像船舶的残骸,永远沉没于漆黑的海底。我不能让历史发生断裂。这便是推动我创作《与父亲书》的力量。